大概是年龄的原因吧,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沉湎于过去,特别是爱回忆儿时的往事。这不,随着兔年的春节越来越近,小时候过年的情景又历历在目了。
我出生于60年代初期,土生土长在农村整整18年,直至高中毕业考入大学。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,生育是顺其自然,所以,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,我家就有兄弟姐妹八个。打我记事起,大多数人家的日子都很艰难。好在我们处于“高上”地区,土地还算比较肥沃,自然灾害的侵蚀相对较少、较小,勉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温饱。在农村,农民辛苦劳累了一年,过年就成了最看重的一件头等大事,也算是给一年劳作来个总结吧。拿出浑身解数,凭本事酬劳自己、犒赏全家、慰问亲朋,从中去体味自豪感、获得感、荣誉感、幸福感。
怎样过年是需要提前筹划、精心准备的。从腊月初一“蹦一蹦”开始,“年”就有形、有影、有声了。再经过蒸、买、扫、炒等几步曲,年味儿就这样一点点浓了起来,直到过年那几天达到高潮。
我们先说“蒸”。一过“腊月二十三糖瓜粘”,家家户户就陆续开始蒸面食了。主角基本上是棒子面白豆馅窝窝头,用模具刻出来的少量白面红豆馅小方包子,其次有粘面切糕、糜子面枣糕、小米面发糕等等,条件好一点的还会蒸三两锅白面大馒头。土地上大自然馈赠的、一直都舍不得吃的各种精细粮食在年前都变成了熟食,放在院内背阴的地方自然冷冻储存在大缸里,随吃随取,一个正月都不会变质。
“蒸”的前奏是“磨”,只有把可蒸的粮食磨成面,才能和枣呀、豆呀、糖精呀搭成美食。于是,一进腊月碾房就成了最热闹的所在。全村最大的一座碾房,建在小学校前、一个大水坑边的高台上。宽敞的碾房内,一东一西两盘石磨,圆圆的磨盘,大大的石碾,每个石碾上一前一后需要两个圆木碾棍,各家自带。石磨昼夜不停,按照排序一家家、一样样耐心地磨着,家人轮换着一步步、一轮轮用力地推着,扫下的粗面由主妇们在大笸箩里一下下、一次次反复地筛着,直至全部成为可以食用的细面。一圈又一圈,转着欢声笑语,转着“不蒸包子蒸口气”的打算,终于转进了热闹的年。
我们再看“买”。买年货是那时最不好拿捏的一件事 ,既简单又复杂。因为钱少,所以简单;因为必须,所以又复杂。至于什么时间去买,如果家里没有出门上班的,只能靠工分的,那就完全取决于生产队年终决算分红的时间。至于买什么、买多少则完全取决于口袋里的钱数。虽然,生产队能分一点儿猪肉,但男人要喝酒,老人想点心,男孩子要鞭炮,女孩子要新衣,还要走亲访友,主妇们是真难啊!但即使再难,一年到头,也得尽量让一家人高高兴兴不是?数着那几个大子儿,左算计右算计,用攥出水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。想要归想要,完全满足所需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就拿做新衣服来说,能挤出一两块布料钱就不错了,全家轮流坐庄,或根据情况调剂。式样裁剪好不好看、手工缝制是否精细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年关家里有人衣服见新了,新年新气象嘛。因为实在舍不得下手,所以,供销社跑了一趟又一趟,付款时心疼得后槽牙都快咬麻了。
现在再说“扫”。“二十五扫房土”,而且真的是扫“土”。炕是土炕,墙是土灰墙,地是砖土地、甚至是纯土地。扫房土是力气活、仔细活,更是脏活、累活,需要分工合作。清扫前要把炕上的、躺柜上的所有东西都搬到院子里,男人们在一根稍长木棍上绑上扫帚,从房顶开始仔仔细细地清扫整个墙面的浮尘和蛛网,然后再跪地掏清躺柜下的积尘。女人们用稍微湿一点的破布一点点清除土炕四边黑褐色的烟熏,然后再将地面喷洒少量的清水防尘除尘。清洁窗户没有玻璃可擦,因为都是用毛头纸糊的,需要擦拭一个个木头格子。清扫结束后,虽然看上去还是土里土气,但角角落落却已经干干净净。摆脱晦气,除旧迎新,女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衣服、被褥大清洗。
再来看“炒”。从腊月初一“蹦一蹦”开始,“炒”就成了家家年前不可或缺的事情。炒花生、炒葵花籽、炒棒子花、炒粉条、炒白薯干,可炒均炒、应炒尽炒。女人们用毛巾包住头,灶堂里点起火,把沙土一点点烧热,再把炒货分别放进铁锅里用铁铲上下不停地翻动。铁铲与铁锅和沙土摩擦,时不时会发出一种让人心中发颤、忍不住打激灵的声响,但这无伤大雅,这种小瑕疵是无法与锅里的香味抗衡的。当浓香飘满堂屋,看到孩子们各个垂涎欲滴、跃跃欲试,大人们的心里是美滋滋的。过年,不就是要“炒”出家的温馨,“炒”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么。
等到蒸、买、扫、炒等各个环节把年味儿全部烘托到位,年就真的来了,如期而至,高潮迭起。
第一个高潮,除夕全家大团圆。那时过年,无论你人在哪里,回家过年都是发自肺腑的一种渴盼,即使路途遥远,即使交通不便,千辛万苦也抵挡不住归家的匆匆脚步,全家人快乐团聚才是过年的真谛。除夕早晨的第一要务是贴春联。把白面熬成浆糊,用高粱苗做的小炊帚细心地刷满春联的背面,刷一张贴一张。堂屋门框一般贴的是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“大海航行靠舵手,万物生长靠太阳”“庆丰年国泰民安,谢党恩幸福美满”之类的内容;住屋墙壁上贴的是“抬头见喜”;躺柜上倒贴“福”字;甚至猪圈上都贴上“肥猪满圈”的祝语。红艳艳的春联,把年的热闹祥和一下子就烘托出来了。
过年了!孩子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,口袋里装上糖果、炒货,高兴地跑着、笑着、唱着、跳着,进东家、出西家,逛南街、遛北街,成群结队,满世界撒欢儿。闹够了,拎上冰车、揣上冰尜,跑到村中大坑宽阔的冰面上,来一场冰上大会战。只见冰车划得飞快,冰尜抽得飞转,从高坡顺势而下打滑溜就像一溜烟儿。对孩子们来说,过年的愿望就是吃好吃的、玩好玩的,就是买新衣、穿新鞋,就是串亲戚、看热闹,如果能得到几毛钱压岁钱会兴奋得小半夜都睡不好觉!
过年的大餐是中午饭,炖猪肉是主打,烩些白菜、粉条、冻豆腐管够,各家再根据自己的条件杀鸡宰鹅;年夜饭,各家根据祖先留下的传统,或肉馅或素馅吃饺子管饱,有三个看点,一是饺子下锅时燃放一挂“小洋鞭”,二是吃饭前晚辈给长辈拜年,三是看谁能吃到那个包着糖果的饺子最有福气。男人们烫一壶老酒,啧咂有声;孩子们狼吞虎咽、大快朵颐;女人们忙前忙后、心满意足。年带来的是团圆,是喜悦,是幸福。
等天一黑,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点起早就制作好的小灯笼,大的牵小的走出家门。灯笼在每条街上流动着、汇聚着,闪闪烁烁,红红火火,给没有路灯的暗夜带来了点点光明,也让酷寒中的孩子们兴高采烈。
守岁是除夕的压轴戏。家家在院子里铺上一层芝麻秸,踩上去“噼啪”作响,寓意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、生活有声有响。全家聚在一起,炕上地下满满一屋,有说有笑,热热闹闹。年轻人嗑着瓜子,吸溜着刚刚脱去冰壳子的大柿子,甜爽痛快;老人们嘴里抿着热水,乐得眯缝了双眼。疯玩了一天的孩子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,最后只剩一些男人在瞌睡中坚守。在那个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视、没有娱乐的年代,守岁,守的是内心的一份宁静,守的是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第二个高潮:初一家族大拜年。按照传统习俗,每年初一最重要的事就是家族大拜年。所有的晚辈都要去给长辈们登门拜年。于是初一一大早,家家户户的小媳妇们一边捯饬自己,一边催男人、孩子们换上最好的装扮,一拨又一拨,一路又一路,各个家族开始挨门逐户大拜年。进爷爷家,出大妈家,一片笑语喧哗。特别是大家族的拜年,一家又一家,交叉重叠,拜年的队伍像滚雪球似的壮大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逶迤前行,喜气洋洋,成了大街上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到最后一家,只能是前门鱼贯而入、后门鱼贯而出了。孩子们吃一颗糖,男人们点一支烟,晚辈恭恭敬敬,长辈高高兴兴,尊老孝亲,其乐融融。
第三个高潮:初二开始的姑爷大拜年和亲戚之间“车轮战”。从初二开始直至正月十五,拜年就从对内转为对外了。正月最尊贵的客是老少姑爷。丈母娘疼姑爷是有讲究的,过年最好的东西早就留了下来,看着闺女一家吃得高兴,心里比蜜还甜。“车轮战”是最有年味的,今日姑家、明日舅家、后日姨家,就连远亲有时间也去看望一下,无论多远,顶风冒雪,乐此不疲。一盒点心、一瓶酒、几个苹果,这是比较豪华的配置。经常是一盒点心“轮”来“轮”去,谁也不舍得吃,碰巧的时候还能再“轮”回原家。没办法,穷就讲究不了。但在这“轮”来“轮”去中,亲戚间感情更深了,亲情更浓了,关系更亲密和谐了。
虽然已过去了四五十年,但儿时的年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骨子里,随着岁月更迭,越品越喜欢和怀念那种独特的味道,那是家的味道,是爱的味道,是乡愁的味道,是让人永远难忘的味道!
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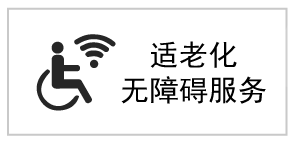
 津公网安备 12011502000093号
津公网安备 12011502000093号
 天津市宝坻区融媒体中心维护
天津市宝坻区融媒体中心维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