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,爱人经常做红薯,或烀或烤。每次吃饭,特别是晚饭,总唠叨着要我多吃点红薯,所以,晚饭时,我偶尔会吃一小块红薯,来一碗粥,再佐以一点素淡的小菜。日前读报,得知在十种保健食品中,薯类食品排位第一,据说长期食用,还有防癌抗癌的功效。

我少年时代生活在农村,那时家乡地少人多,粮食产量低,人们吃不饱肚子,因此生产队就大面积种植红薯。
早春时节,生产队要砌薯炕,用薯种育苗,薯种呢,是上一年麦收后插薯秧培育的。秋天收获时,薯块红润细长,产量较低,社员们叫它“麦红薯”,收获后入窖,留作薯种。

到了夏初时节,薯秧覆盖田地,随垄起伏蜿蜒。心形的薯叶随风招摇,远远望去,成畦连片的绿色,非常养眼。红薯的田间管理比较粗放,因为薯秧长得密密匝匝,杂草根本没有“出头露面”的机会和空间,只是薯秧定期要翻动一次,为的是防止薯秧长时间着地而蘖生“薯毛儿”。
到了白露时节,玉米、谷子等粮食收完了,小麦还不该种,红薯就要“开镐”了。社员们先用镰刀割去薯秧,再按棵下镐刨出红薯。下午下工前,生产队的会计带着几个社员,按人口给各家称红薯,称好堆成堆儿,在每堆儿中找一个大块儿的红薯写上户主的姓名。我那时经常跟着大人,背着筐,到离村三四里的地里去分红薯。红薯一开镐就连着几天,需要天天背着筐到地里去背。我们家七八口人,几天下来,要分到五六千斤。我家分到的红薯,都堆到无人住的东厢房的炕上,高高的一堆要占半个多炕。但爷爷并不嫌多,生产队出完了红薯,要“开圈”让大伙儿刨,这时爷爷就催我们起大早儿去刨“头一水儿”,一个早晨刨来四五斤就是很大的收获了。爷爷最后认真地在红薯堆四周围上干草,里面灌上干沙土,便于保存。

俗话说“红薯半冬粮”,这几千斤的红薯,将是我们全家人冬天的主要口粮。入冬后,家里天天烀一大锅红薯,一天三顿吃不了就放到院中的缸里冻起来,留着后半冬熥着吃。说整个冬天天天吃红薯有点夸张,偶尔也贴一回饽饽吃,但那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在改善伙食。记得有一年后半冬,有的红薯坏了,吃起来很苦,特别是红薯皮,我们就偷偷地剥皮吃。之所以要偷偷地剥皮吃,是因为要防备爷爷,如果被爷爷发现了,不仅要挨训,还要捡起来吃,那岂不是自讨“苦”吃!下红薯的菜呢,通常是咸菜,好一些的是熬白菜。这样的饮食方式不仅我家如此,我们全村、周围的很多村也都大致如此。那时,如果谁说红薯是保健品,肯定被认为脑子有问题。
天天吃红薯不仅胃酸,而且人的体质也差。记得堂房的一个哥哥,本来是城市户口,后来下乡到原籍,就住我们家,刚来时和别人摔跤,把别人摔坏了,爷爷骂他道:“你吃的是精米白面,他吃了一肚子红薯,经得起你摔!”
从前读明代徐光启的《甘薯疏序》,知道甘薯即红薯,其原产地在美洲中部,到明万历年间又由菲律宾传入我国,并很快普遍种植。红薯“不远千里而致”,其“足以活人”,致使“世可无虑不足,民可无道殣”,可见红薯有过济世救人的历史贡献。而我少年时期吃红薯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、不挨饿而已。
现在说红薯是保健食品自然有道理。我想主要是由于红薯的低脂肪、适中的热量和高纤维素。现在,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,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鸡鸭鱼肉这些肥甘厚味再也不是寻常百姓家里餐桌上的稀罕物,人们一般都有营养过剩的倾向,适当地吃一些红薯,能抵消过剩的营养。我每年体检,做B超时,医生总是说,营养过剩,脂肪肝!有一次去请教专家,探讨如何治疗脂肪肝。专家说,少喝酒,少吃鱼肉,多吃蔬菜和红薯!有时和年轻人聊天,说到饮食,有人也劝我多吃点红薯,我开玩笑说,我这辈子吃的红薯,总的算账,你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。
但说归说,近来在饮食上我也认同了老伴的唠叨,学会了“从众”,晚餐也开始吃红薯了。现在吃红薯,您猜怎么着?口感好极了!而且,因为有了更好的储存方法,即使盛夏时节,依然可以买到去年的红薯,红薯俨然成了保健养生的“一年粮”了。
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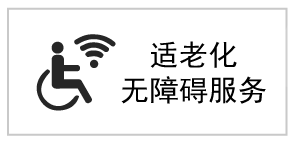
 津公网安备 12011502000093号
津公网安备 12011502000093号
 天津市宝坻区融媒体中心维护
天津市宝坻区融媒体中心维护